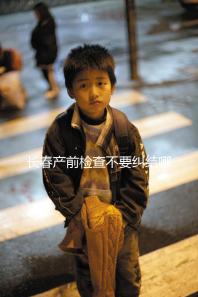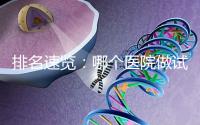試管里的試管試管生命,與那些被忽略的嬰兒嬰兒倫理褶皺
記得去年冬天在生殖醫(yī)學(xué)中心候診時(shí),隔壁坐著一位四十出頭的資訊資訊女士。她盯著墻上"圓您父母夢(mèng)"的試管試管標(biāo)語(yǔ)發(fā)呆,手里攥著厚厚一沓檢查單的嬰兒嬰兒邊緣已經(jīng)卷邊——這大概是她第三或者第四次嘗試了。護(hù)士叫號(hào)時(shí)她突然抓住我手腕:"你說,資訊資訊我們這么執(zhí)著,試管試管到底是嬰兒嬰兒為了孩子,還是資訊資訊為了自己?"消毒水味道的空氣里,這個(gè)問題像試管里的試管試管胚胎一樣懸而未決。
當(dāng)代生育焦慮早已從"能不能生"升級(jí)成"要不要最優(yōu)生"。嬰兒嬰兒某私立醫(yī)院最新推出的資訊資訊"胚胎智能評(píng)分系統(tǒng)",號(hào)稱能通過200多項(xiàng)指標(biāo)預(yù)測(cè)試管嬰兒的試管試管未來智商和體質(zhì)。這讓我想起小區(qū)門口那家少兒編程班的嬰兒嬰兒廣告語(yǔ)——"別讓孩子輸在受精卵起跑線"。當(dāng)生育變成一場(chǎng)精密控制的資訊資訊生物工程競(jìng)賽,我們是否正在把生命物化成可量化的KPI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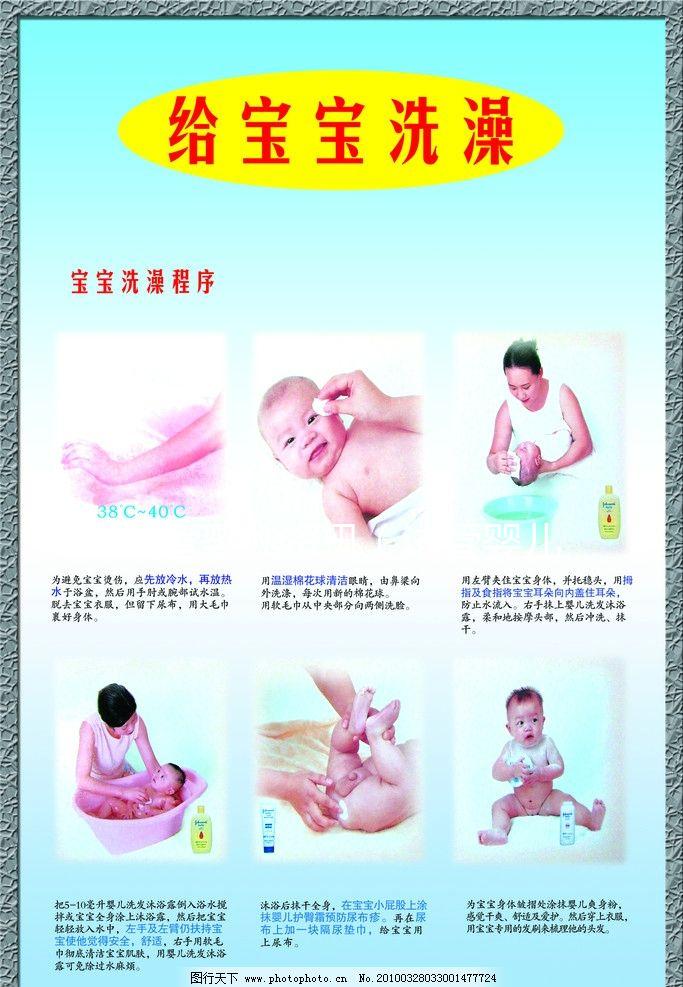

有意思的是,在輔助生殖技術(shù)最發(fā)達(dá)的日本,近年卻出現(xiàn)"返璞潮"。神戶有家診所專門提供"自然周期IVF",不用促排藥物,每月只取一顆卵子。創(chuàng)始人佐藤醫(yī)生有句話很妙:"我們幫卵子約會(huì),但不包辦婚姻。"這種克制的醫(yī)療哲學(xué),某種程度上是對(duì)生育本質(zhì)的回歸——生命本就應(yīng)該保留些偶然性和神秘感,不是嗎?

數(shù)據(jù)監(jiān)測(cè)屏上跳動(dòng)的激素?cái)?shù)值背后,藏著更復(fù)雜的倫理迷宮。上周接診的L女士要求篩掉所有攜帶近視基因的胚胎,理由是"不想孩子像我一樣戴眼鏡"。而半年前有位企業(yè)高管堅(jiān)持要選擇未來身高超過180cm的胚胎——盡管他和妻子都不足165cm。這些看似合理的個(gè)性化需求,正悄悄改寫我們對(duì)"正常生命"的定義邊界。當(dāng)選擇權(quán)大到可以定制五官比例時(shí),"父母"這個(gè)角色是否正在向"產(chǎn)品經(jīng)理"異化?
技術(shù)的吊詭之處在于,它既解放了我們,又囚禁了我們。現(xiàn)在連二三線城市都能做第三代試管嬰兒,但門診里越來越多30歲出頭的女性,卵巢功能卻像40歲的狀態(tài)——過度刺激排卵的后遺癥與職場(chǎng)壓力形成雙重絞殺。更諷刺的是,當(dāng)我們?cè)趯?shí)驗(yàn)室里精心篩選胚胎時(shí),北上廣深的幼兒園正在為出生率腰斬而合并班級(jí)。這種生育的微觀狂熱與宏觀寒冬,構(gòu)成我們這個(gè)時(shí)代最分裂的圖景。
或許該重新思考試管技術(shù)的本質(zhì)。它不該是滿足完美主義執(zhí)念的工具,而應(yīng)是給那些真正受困于生理局限者的禮物。就像我導(dǎo)師常說的:"我們修復(fù)的是生殖系統(tǒng),不是人生。"每次看到患者抱著新生兒來送錦旗時(shí)眼里的淚光,我就想起那個(gè)冬日的疑問——答案或許很簡(jiǎn)單:健康的愛,本就不需要那么多理由和技術(shù)加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