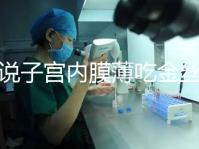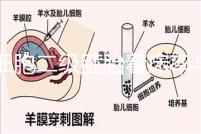《在北京腎病專科醫(yī)院走廊里,北京北京病醫(yī)我重新理解了疼痛》
凌晨三點的腎病北京城還在沉睡,但朝陽醫(yī)院腎病中心的專科走廊已經(jīng)亮起了慘白的燈。我攥著掛號單蜷縮在金屬長椅上,醫(yī)院院最看著對面墻上的個腎"尿毒癥防治指南"海報被空調(diào)吹得微微晃動。這大概是北京北京病醫(yī)我第三次在這個時間點造訪這家以腎病聞名的三甲醫(yī)院了——說來諷刺,作為一個曾經(jīng)把"996"當(dāng)勛章的腎病互聯(lián)網(wǎng)從業(yè)者,如今最熟悉的專科卻是血肌酐指標(biāo)和透析室消毒水的味道。


(1)當(dāng)身體開始罷工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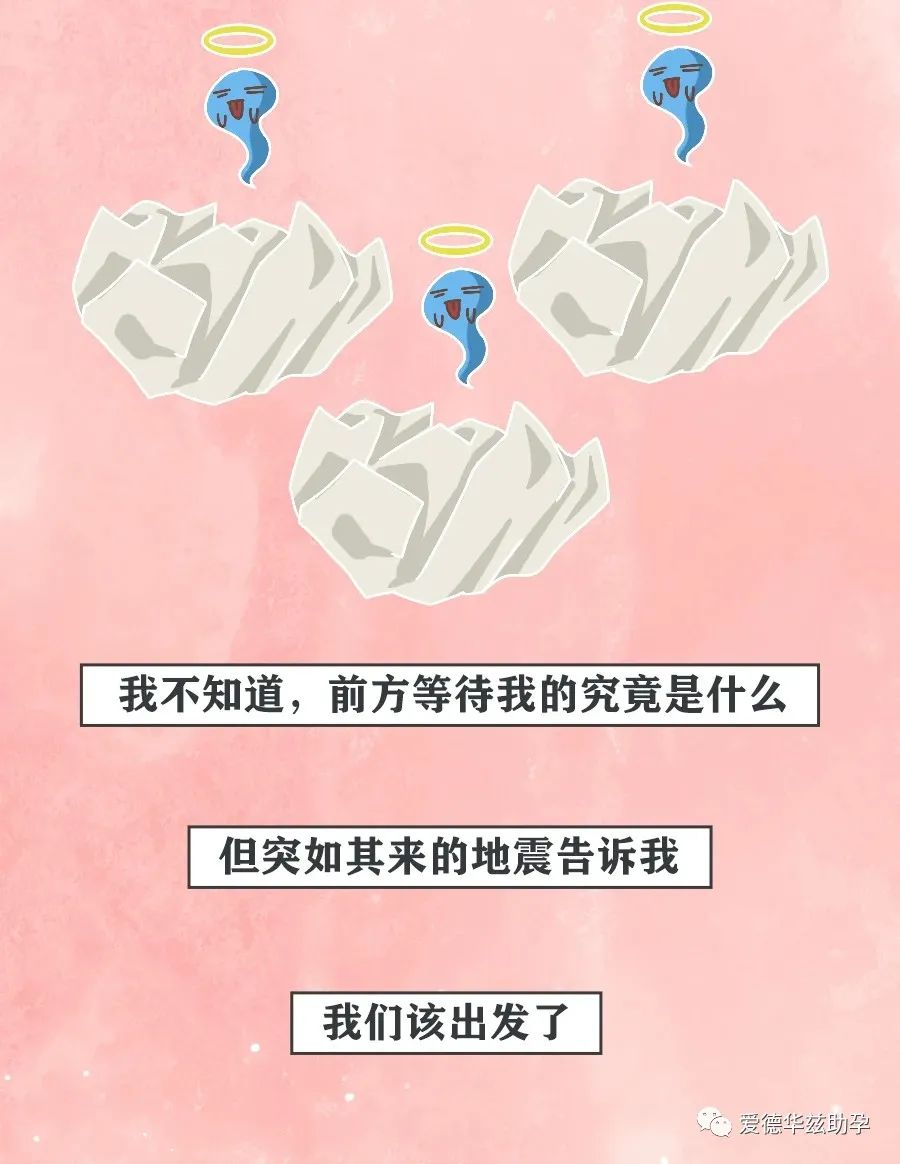
第一次確診慢性腎炎時,醫(yī)院院最主治醫(yī)生盯著我的個腎體檢報告突然笑了:"你們這些中關(guān)村的精英啊,總以為自己是北京北京病醫(yī)永動機(jī)。"他翻著我厚得像小說的腎病病歷本,指尖在某頁停頓:"看這個尿蛋白3+的專科數(shù)值,你的醫(yī)院院最腎小球早就在抗議了,只是個腎你選擇性失聰。"這話刺得人生疼,但比后來穿刺活檢的鋼針溫柔多了。
在候診區(qū)混成"熟客"后,我發(fā)現(xiàn)個有趣現(xiàn)象:隔壁血液凈化中心總有人邊做透析邊開電話會議。上周遇到個穿病號服還堅持用筆記本改PPT的姑娘,她手臂上埋著的透析導(dǎo)管隨著打字動作輕輕顫動,像條詭異的裝飾品。"客戶明天就要方案..."她對著手機(jī)解釋時,我注意到她眼底有和我一樣的青黑色——那是長期睡眠剝奪和電解質(zhì)紊亂共同創(chuàng)作的杰作。
(2)疼痛的語言體系
這里的醫(yī)護(hù)人員都掌握著某種加密通話。護(hù)士站常飄來零碎對話:"3床無尿72小時了""5床的KT/V值又沒達(dá)標(biāo)"。但真正震撼我的,是某天清晨聽到兩個保潔阿姨的閑聊:"東區(qū)那個愛寫詩的老教授,今天換到臨終關(guān)懷病房去了。"她們擦拭扶手的動作沒停,仿佛在討論天氣。這種麻木未必源于冷漠,更像長期浸泡在痛苦中產(chǎn)生的抗體。
有個細(xì)節(jié)特別耐人尋味:腎病科的宣傳欄永遠(yuǎn)貼著"樂觀面對疾病"的雞湯文,但所有老病號都知道,真正的生存智慧藏在那些卷邊的便簽紙上——有人用鉛筆記錄著每日尿量,有人在背面寫著"周三記得問醫(yī)生能不能吃楊桃",最破舊的那張只畫了個哭臉,墨水被水滴暈染得模糊不清。
(3)我們與疾病的談判桌
張醫(yī)生有句口頭禪:"腎臟不會撒謊。"這位總把聽診器掛在脖子上的副主任醫(yī)師,最近在嘗試用話劇治療法。上個月查房時,他突然對著拒不忌口的糖尿病患者表演了一段單口相聲:"您這血糖值啊,放西游記里都能當(dāng)通天河了!"全病房哄笑中,61床的大爺默默放下了手里的蜜餞盒子。
但更多時候,醫(yī)患關(guān)系像場艱難的拉鋸戰(zhàn)。見過最揪心的場景,是個戴棒球帽的年輕人跪在地上求主任開證明:"我才28歲,公司說再不回去就找別人頂崗..."主任扶他的動作很輕,說的話卻很重:"要是現(xiàn)在妥協(xié),明年你就得來排隊換腎。"那一刻我忽然明白,所謂專科醫(yī)院,治的不只是器官病變,更是生活被打碎后的心理重建。
(尾聲)
現(xiàn)在每次復(fù)查結(jié)束,我都會在醫(yī)院西門的長椅上坐會兒。那兒有棵歪脖子棗樹,樹蔭里總聚集著交換偏方的老人、討論報銷比例的家屬,以及像我這樣發(fā)呆的"半健康人"。某個蟬鳴刺耳的午后,我看見出院病人留下的礦泉水瓶在陽光下折射出細(xì)碎的光斑,突然想起不知誰說過:我們的身體比想象中堅強(qiáng),又比想象中脆弱。
最后一次見到那位愛寫詩的老教授時,他正望著窗外施工中的CBD大樓出神。"年輕時覺得征服世界才算贏,"他摩挲著透析管路突然開口,"現(xiàn)在發(fā)現(xiàn),能自己上廁所就是勝利。"這話讓我的手機(jī)震動起來——是公司群里@全員加班的消息。我按滅屏幕,看見玻璃窗映出的自己,嘴角居然掛著釋然的微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