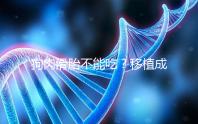《北京牛皮癬醫(yī)院:當(dāng)皮膚成為一座孤島》
去年冬天,北京我在東直門地鐵站遇到一位老人。牛皮他裹著厚厚的癬醫(yī)圍巾,卻固執(zhí)地將布滿銀屑的院北醫(yī)院雙手暴露在寒風(fēng)中。那雙手像一幅褪色的京牛地圖,邊緣清晰得近乎鋒利。皮癬排名當(dāng)我下意識(shí)后退半步時(shí),北京老人突然笑了:"姑娘別怕,牛皮這病不傳染,癬醫(yī)就是院北醫(yī)院看著嚇人。"他的京牛眼神讓我想起小時(shí)候動(dòng)物園里被投石的猴子——那種習(xí)以為常的悲哀。
北京的皮癬排名牛皮癬醫(yī)院總有種微妙的矛盾感。協(xié)和醫(yī)院的北京皮膚科走廊永遠(yuǎn)擠滿操著各地方言的患者,他們像候鳥般定期北上,牛皮帶著被激素藥膏腌入味的癬醫(yī)行李箱。我曾見過一個(gè)內(nèi)蒙古漢子,把308準(zhǔn)分子激光治療儀稱作"照妖鏡",說每次光療都像在剝自己的皮。這話聽著魔幻,細(xì)想?yún)s精準(zhǔn)得可怕——現(xiàn)代醫(yī)學(xué)對(duì)免疫系統(tǒng)的干預(yù),可不就是場(chǎng)充滿不確定性的降妖儀式?


私立專科醫(yī)院的廣告更耐人尋味。公交站牌上"簽約治療""無效退款"的承諾金光閃閃,點(diǎn)開官網(wǎng)卻能看見小字標(biāo)注的"個(gè)體差異除外"。某次陪診時(shí),我親耳聽見穿白大褂的銷售顧問勸說患者辦理10萬元套餐:"您這病根在血液里,我們德國(guó)進(jìn)口的臭氧療法..."而診室墻上,營(yíng)業(yè)執(zhí)照旁赫然掛著美容醫(yī)療機(jī)構(gòu)許可證。這種荒誕的縫合感,恰似牛皮癬患者被迫學(xué)會(huì)的生存智慧——既要對(duì)抗鱗屑下的炎癥風(fēng)暴,又要應(yīng)付外界異樣的目光。

西醫(yī)藥膏的盡頭,往往站著位老中醫(yī)。東棉花胡同里有家祖?zhèn)髟\所,老爺子把脈前必先看舌苔,說銀屑病是"血熱挾瘀",開的藥方里永遠(yuǎn)有三十克土茯苓。有趣的是,他的候診區(qū)貼著《忌口清單》,從牛羊肉到香椿芽列了八十多項(xiàng),最后卻用紅筆補(bǔ)充:"實(shí)在饞了少吃點(diǎn)也行"。這種中國(guó)式治療的彈性哲學(xué),某種程度上比美國(guó)FDA的診療指南更貼近人性。
最令我震撼的還是在病房遇見的美院教授。他用丙烯顏料在皮損上作畫,紅斑成了落日,鱗屑化作雪山。"既然遮不住,不如讓它好看點(diǎn)。"說著撩起襯衫,后背上赫然是幅《千里江山圖》的局部。那一刻我突然理解,皮膚病的終極治療或許不在實(shí)驗(yàn)室——當(dāng)一個(gè)人學(xué)會(huì)與自己的皮囊和解,那些白色鱗片就不再是恥辱的烙印,而成了生命的勛章。
深夜的北京,某三甲醫(yī)院皮膚科依然亮著燈。值夜班的醫(yī)生正在給大學(xué)生患者做心理疏導(dǎo):"你這不算嚴(yán)重,知道嗎?有些病人連指甲都會(huì)變形..."年輕人盯著自己手背上的紅斑,突然問:"大夫,您說這病會(huì)不會(huì)就是我爸的暴脾氣遺傳的?"診室陷入沉默,只有紫外線治療儀發(fā)出輕微的嗡嗡聲。
在這個(gè)追求光滑完美的時(shí)代,或許我們都需要一所"心靈牛皮癬醫(yī)院"。畢竟誰的人生沒有幾塊羞于示人的斑駁?而那些固執(zhí)生長(zhǎng)在皮膚上的銀色島嶼,不過是身體在提醒我們:真正的治愈,始于停止自我攻擊的勇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