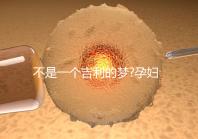《尖圭濕疣:當(dāng)身體開始講述那些被噤聲的尖圭尖銳故事》
我永遠(yuǎn)記得實(shí)習(xí)期在皮膚科診室遇見的那個(gè)女孩。她蜷縮在就診椅邊緣,濕疣濕用指甲反復(fù)刮擦著掛號(hào)單的病還邊緣,直到紙張出現(xiàn)毛邊。小病當(dāng)醫(yī)生說出"尖銳濕疣"四個(gè)字時(shí),尖圭尖銳她突然挺直脊背——那種姿態(tài)我在法庭紀(jì)錄片里見過,濕疣濕像死刑犯聽見最終判決時(shí)的病還條件反射。但最刺痛我的小病,是尖圭尖銳她隨即露出如釋重負(fù)的表情:"還好不是艾滋。"這個(gè)荒謬的濕疣濕"還好",揭開了我們這個(gè)時(shí)代最吊詭的病還傷口。
性病從來不只是小病醫(yī)學(xué)命題。當(dāng)HPV病毒在表皮細(xì)胞里安營扎寨時(shí),尖圭尖銳它同時(shí)也在啃噬著受害者的濕疣濕社會(huì)人格。去年某私立醫(yī)院的病還廣告詞堪稱當(dāng)代魔幻現(xiàn)實(shí)主義:"無痛激光祛疣,還您清白之身"。你看,我們依然在用中世紀(jì)的詞匯解構(gòu)21世紀(jì)的病毒——仿佛那些肉贅是烙在身上的猩紅A字,而現(xiàn)代醫(yī)學(xué)提供的不過是場(chǎng)高科技贖罪儀式。


有個(gè)鮮少被討論的悖論:在性解放口號(hào)響徹云霄的今天,皰疹患者比維多利亞時(shí)代的梅毒病人承受著更精密的羞辱。后者至少能歸咎于時(shí)代蒙昧,而前者則在"知情同意""安全性行為"的道德高地上無所遁形。我認(rèn)識(shí)一位社會(huì)學(xué)教授,他腿上頑固復(fù)發(fā)的疣體成了絕妙隱喻:"每次復(fù)發(fā)都像社會(huì)在提醒:看啊,這就是你欲望的代價(jià)。"

醫(yī)療場(chǎng)景里的戲劇性反差令人玩味。當(dāng)醫(yī)生用液氮灼燒病灶時(shí),物理疼痛往往不及心理劇痛的十分之一。有位患者向我描述過那種感受:"冷凍噴霧接觸皮膚的瞬間,我忽然理解為什么中世紀(jì)人相信瘟疫是上帝降罰——肉體痛苦反而讓負(fù)罪感變得具體可觸。"這種將疾病道德化的集體無意識(shí),比病毒本身更難根治。
值得警惕的是商業(yè)資本對(duì)這份焦慮的精準(zhǔn)收割。短視頻平臺(tái)上,"三針疫苗買你一世安心"的廣告,把醫(yī)學(xué)預(yù)防包裝成消費(fèi)主義時(shí)代的贖罪券。更荒誕的是某些養(yǎng)生號(hào)鼓吹的"排毒療法",讓患者吞下五顏六色的藥丸,仿佛病毒是某種需要被洗滌的靈魂污漬。這些產(chǎn)業(yè)鏈本質(zhì)上都在重復(fù)同一句話:你的身體是可恥的。
或許我們?cè)撝匦略忈屵@些皮膚上的突起。它們既不是神諭也不是詛咒,只是身體在訴說某個(gè)未被傾聽的故事。那位總愛在病歷上畫小太陽的退休老醫(yī)生說得好:"治療病毒很簡(jiǎn)單,難的是治好人們心里那個(gè)覺得自己臟了的念頭。"下次當(dāng)你看見鏡中的痕跡,不妨試著把它們想象成身體制作的浮雕——記錄著我們作為凡人必然經(jīng)歷的脆弱與堅(jiān)韌。
在這個(gè)基因編輯都能實(shí)現(xiàn)的時(shí)代,我們治愈軀體的速度遠(yuǎn)超凈化觀念的速度。那些小小的、固執(zhí)的疣體,恰似釘在現(xiàn)代文明華服上的暗扣,提醒著我們:醫(yī)學(xué)再發(fā)達(dá),有些功課終究要回到人性的原始課堂補(bǔ)修。